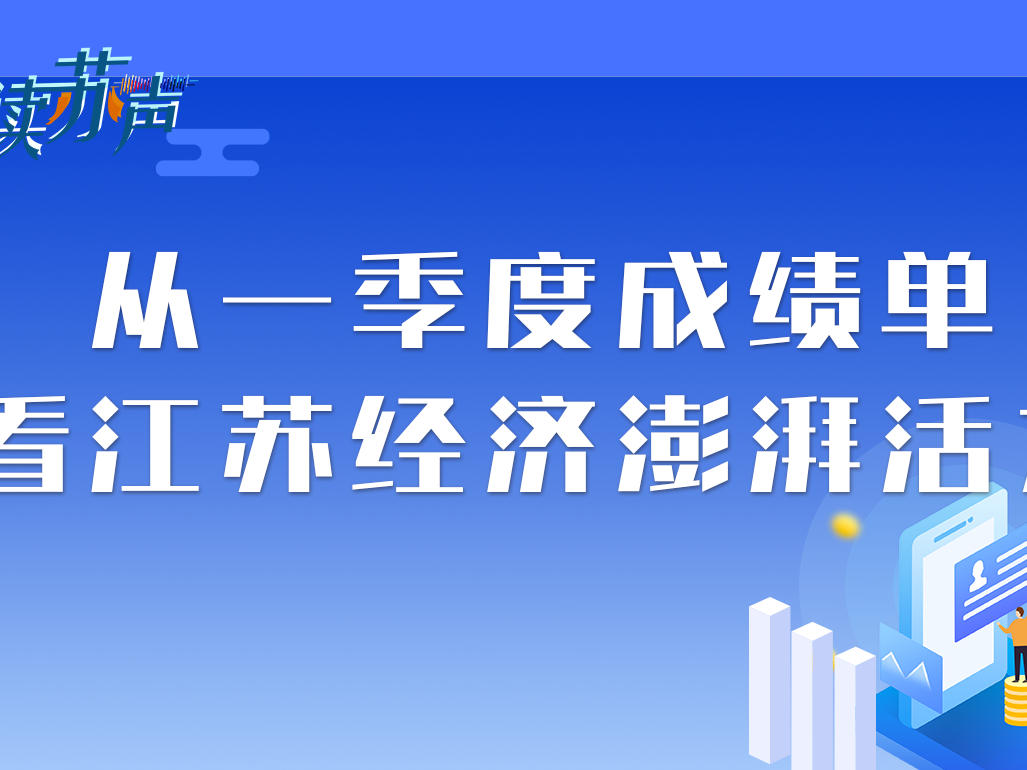今日,有南大校友朋友圈曝光南大教授董健昨日去世的消息,记者随后从南大证实了这一消息。其学人精神引发老师、学生纷纷缅怀。

董健教授是著名戏剧学家,他的学术贡献在戏剧以及社会文化领域均有较大影响。他开创性地提出戏剧文学的现代化研究,追求思想启蒙和独立思考,也成为南京大学戏剧影视学科的标志性传统。
董健,1936年1月出生,山东寿光人,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荣誉资深教授,曾任南京大学副校长、文学院院长,兼江苏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中国话剧研究会副会长。
在研究者心目中,董健教授是一个坚持现代性和人文情怀、既大气又有才气的学者,是坚持教学科研,引领南大文学院走向正轨的关键人物。董健教授坚持学术的基础性和前瞻性,是负责任的知识分子。
1944年,8岁的董健初入学堂,由于营养不良,看起来瘦弱矮小。在讲究耕读传家的山东,董健常被人说“干不了农活,只适合读书”。
尽管已经过去了大半个世纪,董健依然清晰地记得自己刚开始读书时的情形。学堂的学习经验,也直接影响了董健日后的教育理念,许多学生都用“由浅入深”、“潜移默化”等方式来形容作为老师的董健。
1962年本科毕业后,董健在南京大学读了三年研究生,成为陈中凡教授的学生,研究中国戏剧史。1965年,董健毕业后留校任教,教授样板戏的课程。不久“文革”爆发,地主家庭出身的董健受到一定冲击。
“文革”后期,青年教师董健被调入江苏省革命大批判组,专门写批判文章。当时,《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贺敬之来到江苏,要求省革委会写一篇批判田汉“人性论”的文章。革委会成员忙了将近一年,结果文章过不了关,一句话都没有刊登。但在写文章的过程中,由于董健通读所有关于田汉的资料,反而成为日后写作《田汉传》一书的积累与思考。
文革结束后,《田汉传》出版发行,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连印三版,发行量非常大,许多读者都反应作品描绘了一个真实的田汉。

1978年,董健才真正开始自己的学术研究。他大量阅读文献资料,撰写各类文章,囊括学术论文、文学评论与文化批评等各种理论思潮。这些不仅成为董健不断探索现代意识、启蒙理性、人文精神的学术立场,也展现出他不断追求真实、追求真理的思想脉络。
改革开放以来,董健更是迎来了学术的高峰期,重点研究戏剧艺术与中国当代文学史两个领域,留下了《田汉传》《陈白尘创作历程论》《戏剧艺术十五讲》《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等著作。
1987年,董健被聘为南京大学教授,在近40年的时间里,桃李遍地,立德树人。
此后,董健不仅坚持潜心研究戏剧艺术,同时担任南京大学副校长一职,他曾说自己是“大学失魂的见证人”,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呼唤大学的精神归位。
新世纪以来,花甲之年的董健依然奔走在学术的道路上,探讨中国戏剧的现代化道路问题,勇于谏言,并热切地呼唤现代意识与启蒙理性。出版《文学与历史》《戏剧与时代》、散文集《跬步斋读思录》《跬步斋读思录续集》等,主编大型工具书《中国现代戏剧总目提要》《中国当代戏剧总目提要》,并发表近千余篇学术论文。在数十年的理论研究与教学生涯中,为中国现当代戏剧和文学学科的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由陈白尘与董健领衔主编的《中国现代戏剧史稿》《中国当代戏剧史稿》被学术界誉为近30年来中国现当代戏剧研究的一套重要著作,它包含了对中国现当代戏剧发展的种种思考和大量第一手资料的搜集整理,是对20世纪中国现当代戏剧的整体描述和剧目梳理,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和重大的学术价值。
董健晚年视力日益减退,虽然读书和写作都受到一定的影响,但却依然不愿放弃学习与思考。在他看来,崇高的批判精神让人文主义的火种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谨以此文纪念董健先生。

高校颓风日甚的深层原因
文 | 董健
来源 | 《中华读书报》2008年4月9日
晚明首都南京的繁华,不过是大厦将倾的回光返照,明人绘《南都繁会图卷》就是描写这种繁华的。在《中国新闻周刊》上读到曹红蓓的《在烟花烂漫中坠落》一文,觉得她用这个标题来揭示这幅画卷所蕴涵的文化意味,不仅很到位,而且发人深思。
的确,事物的败落,尤其是人的精神的败落,往往都是在表面繁华的“热闹”中发生的。目前中国的学术界(我主要指人文和社会科学)不就颇有些“在烟花烂漫中坠落”的样子吗?至少在大学文科各种“热闹”的烟花烂漫的景象中,我们正遭遇着精神的麻木和萎缩。
譬如曹文中说到,“士子”爱作秀,拿学问当“玩物”,“士风”浮薄;文人以自己的“知识”和“科技”优势上市行骗,等等。她特别提到,在“钱神”的威力下,斯文扫地,社会风气浮薄而虚夸,为了多捞“好处”,“士”(学者、文人)与“商”(买卖人、企业家)便“互动”起来:“士很想介入商业活动,商则乐于标榜自己的文化品位。” 这“士商互动”,简直活画出了当今我国学术界精神麻木和萎缩的一个“奇观”。
不是吗?官员(或曾为“士”)和商人(企业家)手中有“权”和“钱”,便向“文”靠拢,弄个硕士、博士、博士后的头衔戴戴,甚至被大学“特聘”为教授、博导之类,也并不是什么难事,而且时髦得很,在“业内”可增加竞争获胜的筹码;而大学的某些教授、博导们则时时事事觊觎着“权”和“钱”,一方面视“官位”为至宝,怕官、羡官、依附官,不忘“中国文化是侍奉主子的”,一方面为了“兼职”赚钱,敢目无校纪,随意缺课或叫研究生代课,即使自己上课也忘不了与“商”的联系,手机在课堂上就堂而皇之地响起来。难怪民间短信有云:“教授慕官而又像商人,官员、商人则很像教授”。
但我认为,这却不能怪“官”和“商”那一方。他们追求“文化品位”完全是正当的,他们中的有才华者要是真做起学问来,也不一定比教授、博导们更差。我就读过官员的“学术著作”,并不比学术界弄出的那些伪劣之作差到哪里去。
问题恐怕主要出在“士”这一方。正是因为这些“士”们不好好做学问,把学术庸俗化、商品化了,或者工具化、政治化了,一句话,是他们糟蹋了、矮化了为学之道,才使得本来不学无术的“官”和“商”轻而易举地得到了用以“标榜自己的文化品位”的那些空名和虚假的头衔。
要说风气坏,那是双方联手搞坏的。
改革开放30年来,学术研究是有很大进步的,尤其是80年代,在思想解放运动中,批判了多年扼杀学术精神的极左思潮,学术的“自由”和“独立”精神得到鼓励和支持,知识分子曾一度恢复“五四”启蒙主义传统,认认真真地做学问。那时大学里风气好,学风正,研究成果虽不是很多,但质量还是可以的。
然而90年代以后,物质方面、硬件方面在一天天地强起来,而精神方面、软件方面却一天天地弱了下去。我在触人多思的“世纪之交”发表过《失魂的大学》专议此事(见《跬步斋读思录》,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七八年过去了,学术界颓风日甚。各种渠道的科研“项目”和“课题”越来越多,经费投入的力度和学术“成果”的数量都甚可观,五花八门的“学术”活动(研讨会、规划会、新书首发式等)既隆重,又频繁。然而看看那些“热闹”上市的这“工程”那“工程”的大量“作品”吧,有的弥漫着“官腔”,有的充满了“商气”,以至抄袭剽窃、胡编乱造,真是叫人不敢恭维,其中有不少被人们称之为“文化垃圾”。
显然,这样下去,不管“核心刊物”有多少“大作”登出来,不管“标志性产品”装帧多么精美,学术界也不可能对社会进步、人类文明做出什么有价值的贡献。从目前流行的管理模式和大多数研究者的精神状态来看,实在不敢预期短时间内摆脱此一颓势的可能。

从“投入”到“产出”有一整套长期形成的管理体系,这一体系从90年代以来更加细密和强化,它制约着种种申报、立项、拨款、评奖的规则和“潜规则”,直接关系到研究者的“生计”(职级评定、生活待遇),能从根本上消磨以至摧毁学术研究最可宝贵的精神——“自由”与“个性”,批判与创新。
尽管许多人常把陈寅恪的名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挂在嘴上、写在笔下,然而一旦被纳入这个管理体系,面对具体的“利益”(“名”或“利”),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看着学术研究的质量大幅度地下降,看着学术风气的浮薄、虚夸,我深深感到当代知识分子的大溃败!他们对这个管理体制也有抵制和反抗,但失败之后就是无奈地顺从和认同,就是“依附”。
正是在这种顺从、认同和依附中,鲁迅所说的那种知识分子的“真性情”消退一尽,他们探求真理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逐渐麻木,逐渐萎缩。在麻木中萎缩,在萎缩中麻木。所谓“麻木”,就是失去了对事物的感受力与对文化高下、艺术美丑和道德善恶的分辨力,说白了就是黑白不分、是非难辨;所谓“萎缩”,就是失去了那种超越既定“文化秩序”的想象力与对流行的“定见”、“陈见”、“偏见”、“俗见”的怀疑和批判的能力。这二者是互相交叉、互相联系、同步发生的,都是在僵化的管理体制之下,学术丧失“自由”与“个性”的结果。这一切给管理者的报复就是学术园地里“生产力”的下降。

文科的“生产力”主要就是人在精神上的批判创新能力,要靠实践的检验和历史的淘洗,才能知其真伪强弱。这就大有空子可钻。当学术研究的真正“生产力”严重下降,可是“领导”和“主管部门”又要“多出成果”以标榜“政绩”时,怎么办?于是大家都一窝风地去多发文章、多出书。文章要发在“核心刊物”上;书要弄些“大部头”的;为达此目的,不惜花大钱。一块砖头那么厚的书,还算不上“大部头”,难以充当“标志性产品”,要摆在书架“一大排”,放到桌上“一大摞”才行。其实,只有工具书、资料书才可以这么办,而这又怎么能取代有独创性的个人学术著作呢?至于说到以“核心刊物”发表率评估科研,这种制度恐怕已经“异化”为一种中国的学术之“癌”了。说它是“癌”并不过分,因为它已经成为吞噬学术精神的可怕“细胞”。现在,偶见的学术佳作可能发表在非核心刊物上,而乘机牟利的“核心刊物”却常常发一些质量并不高的文章。
然而,只认“核心”,只重“大部头”,只提倡“大兵团作战”,严重忽视个人的、有独创性的学术研究。结果,无奈“依附”了体制的知识分子,其“精神”便渐渐麻木起来,并随之萎缩下去。麻木加萎缩等于平庸。于是,研究项目、课题无个性、无特点,雷同化、简单化,在低水平上重复——这等于一部生产的机器在空转。
但检查评估起来,“成绩”多多,既出了“成果”,又出了“人才”。表面的“繁荣”(热闹)掩盖着真正的虚假与平庸。这时,教授、博导们一个个都“避免了个人主义”、“服从了大多数”,既有了“名”,又有了“利”,走上了一条“最安全”的无“学”而有“术”的路——即失去了学术精神,仅怀谋生之“术”的伪知识分子的道路。

写到这里,忽然想起清末启蒙主义思想家龚自珍“将萎之花,惨于槁木”的话。在那样的世风下,“人心混混而无口过也,似治世之不议”,举世平庸、秩序严密,但是,“庠序无才士”——学校里没有有才华、有创造精神的知识分子。更为可怕的是,即使有“才士”,也往往被“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这种“戮”,并非消灭肉体,而是“戮其心”。戮什么心呢?“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
我们应该扪心自问:关系到知识分子良知存灭的这“六心”,我们被“戮”过吗?我本人可以坦言,我是被“戮”过的,正在努力恢复中,而且一面恢复一面还在被“戮”着。看来,没有真正的体制改革,没有一场“五四”式的现代启蒙运动,我们是难以复此“六心”,从精神麻木和萎缩的邪路上返回的。
来源:综合江苏文学、群学书院 编辑:张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