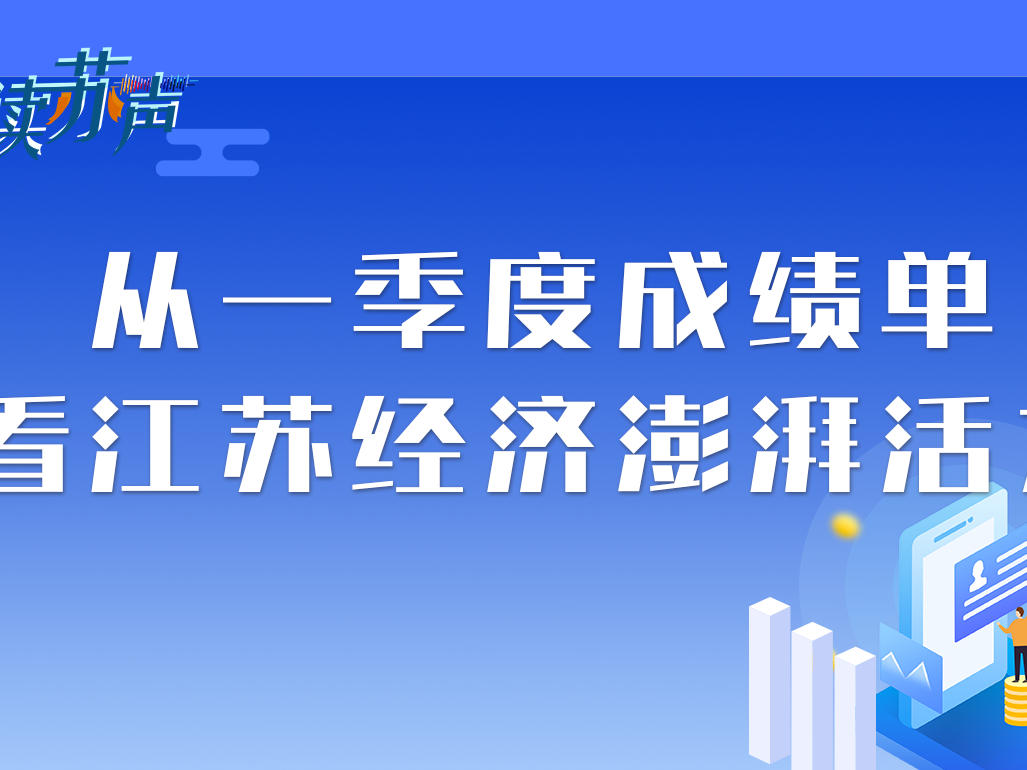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作者:高满堂 李洲
简介:《老酒馆》讲述了上个世纪初闯关东来的山东人陈怀海,历经磨难,最后落脚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大连开酒馆谋生计,并利用老酒馆结交抗日志士,传播爱国思想,与殖民者斗争的故事。它以一个小小的酒馆为舞台,上演了一幕“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传奇大戏。酒馆虽小,却激荡历史风云。
12.假王爷下饵骗吃喝
转眼就是冬天了。厚门帘一挑,大高个穿着棉衣戴着棉帽走进老奉天饭馆坐下。贺义堂赶紧迎过来招呼。
大高个说:“贺掌柜,咱们可认识很久了,你觉得咱们处得怎么样啊?”贺义堂说:“挺好的。”“我记得你说我们处得跟自家人一样,自家人说话不用外道。”
“那是,您有吩咐尽管说,我照办。”
大高个低声说:“跟你直说吧,我碰上点棘手事,又赶上手头不宽裕,想从咱们的家里拿点钱。”他把“咱们的家里”几个字特别加重了。贺义堂沉默着。“半月后连本带利一并还。”大高个说着掏出手串放在桌上,“这宝贝放你这儿吧。”
贺义堂摆手:“爷,这宝贝太金贵了,我怕拿不住。”大高个说:“押你这点东西,我拿钱也拿得踏实。赶紧找明白人,看看我这宝贝值多少钱,然后你就给我拿多少钱出来,要是你手头没那么多钱,就管朋友筹措点吧。”“您把这宝贝典给当铺,不就有钱了吗?”“有自家人在,我用得着去当铺典钱花吗?这不让外人笑话吗!这事就拜托你了,越快越好。”
那正红来当铺当一幅画。董掌柜俯身仔细审视:“这么好的东西,舍得?”那正红说:“放家里怕遭贼惦记。”董掌柜笑了笑:“卖了多好,钱更多。”那正红说:“卖了就买不回来了。放你这儿,说不定啥时候我就把它赎回来。”那正红把钱揣进怀里走出去。
当铺伙计撇嘴:“还怕遭贼惦记,我看他是穷得没招了。他在咱这可典了不少东西,一件也没赎回去过。”董掌柜说:“那人脸皮薄,看破别说破。”
那正红走在街上,迎面碰到贺义堂,贺义堂着急道:“那爷,我可找到您了!他不是从我这拿了不少钱吗,转眼人就没影儿了,半个月,明天就到日子了,他要是不还钱,我可咋办?”
那正红说:“那手串在你手吧?有宝垫底,何惧之有?拿的钱是不少,可对人家来说,是九牛一毛上的毛尖尖,你就放心吧。”
半个月过去,欠债的人没影儿,两个讨债的倒是来了。双方拉锯扯皮老半天,最后敲定,贺义堂一个礼拜后还钱。
贺义堂魂不守舍,来到那正红家讨主意:“那爷,您跟他热乎得不得了,好得跟一个人一样,怎么会连他住哪儿都不知道呢?”那正红说:“人家是王爷,自己不说,我能问吗?那不是以下犯上吗?”
贺义堂摇头:“都啥年月了,还说……那爷啊,我看您跟那王爷交情不错,要不您替他把钱还了?”那正红说:“我俩是交情不错,可我也没那么多钱。”
贺义堂说:“实在不行,我就去老当铺把那手串典了。”那正红说:“少掌柜,这事你可得三思。那手串是王爷的稀罕之物,你要是给典了,王爷会不高兴。”
贺义堂说:“他要想高兴,就赶紧把钱还了!我不是背后碎嘴子说道人,他要是有钱,犯得着管我借吗?”
那正红说:“谁都有一时手紧的时候。放心吧,他就算兜里没钱,家里的宝贝东西多着呢,那手串是摆在面上的,怕看的都在家里藏着呢,随便拿出一件来,都能晃瞎你的眼!再等等吧,说不定就这几天来了个峰回路转。”
没过三天,贺义堂在街上还真的碰上大高个了。大高个说:“我去家里找你,你不在,没想到在这碰上了。”贺义堂说:“爷,您的手串还在我那儿呢,那东西金贵,您赶紧拿回去吧。”
大高个说:“我找你就是为了这事。贺掌柜,实在不好意思,我碰上了点急事,没按时回来。手串拿来吧。”
二人来到老奉天饭馆,贺义堂把手串放在桌子上。大高个拿起手串仔细查看,还要了杯水喝着:“贺掌柜,我欠你多少酒菜钱啊?不要客气,把账簿拿来算清楚,我一并结了。”福六拿来账簿。大高个翻开账簿看着,不住地点着头:“好,一笔一笔,清清楚楚。”他一抬手,把手套扫落在地,他俯身欲捡手套。贺义堂俯身捡起手套,放在桌上。大高个拿起手套掸了掸,站起说:“把手串收好,我这就回去取钱。在这等着,我速去速回。”
可是大高个回家取钱,一走又没影儿了。贺义堂一直等到街上灯火闪烁,也没有等到大高个。
没有别的办法,贺义堂只好去当铺当掉那手串。董掌柜借着阳光仔细打量着手串,老半天,他一皱眉把手串放在柜台上,看着贺义堂说:“拿走吧。少掌柜,我可给你留着面子呢。”
贺义堂奇怪:“您这话啥意思?我不明白啊。”董掌柜说:“非要我点透不可吗?少掌柜,这是假的!”
贺义堂愣住了:“不对啊,您都看过两回了,怎么可能是假的呢?您是不是看走眼了?”董掌柜说:“我能开了几十年当铺,全靠这双眼睛,前两回都是真的,这回是假的,千真万确,走不了眼!我问你,那天你来找我,问这手串值多少钱。从我店里出去后,谁还碰过它?”
贺义堂回忆着:“我把它揣兜里,从您这出去,就回家了,然后就把它藏起来了,没人碰过,我家人都没碰过啊。我想起来了,这手串的主人碰过它。”
董掌柜说:“你给我讲讲,详细点。”他听了贺义堂讲的经过后点点头,“不出所料的话,就是这手串的主人耍的手段。他趁你捡手套的时候,把手串调包了!”
贺义堂说:“我明白了,他又喝水又要看账簿,就是想把我支走,一看我没走,就故意把手套碰掉地上了。”董掌柜说:“那人的手段如此高明,是江湖上的老骗子,他就凭这个手串到处行骗。我听说过这样的骗术,今天算是见识到了。”
贺义堂把受骗的事告诉那正红,那正红说:“都怪我眼睛瞎了,要不你不会遭此大难。”贺义堂凄然一笑:“谁也不怪,只怪我头上顶了个‘贪’字!”
————————
贺小辫紧靠着炕柜坐着:“贺义堂啊贺义堂,你这一回来,我的养老钱搭进去了,眼下这套房子也不保了,你爹我就剩这套房子了,要是再倒腾出去,那我这辈子就白玩儿了!”贺义堂跪在贺小辫近前:“爹,我也不想把房子赔进去啊,可是那么多钱,我实在拿不出来。爹您放心,只要儿子还活着,就不能让您冻着饿着……”
“放你娘的屁,我就一句话,这房子不能给!”贺小辫掀开炕柜,掏出房契紧紧抱在怀里,“我就抱着它,看谁敢来拿!”
贺义堂犹豫良久只好交代:“爹,您手里那房契……是假的。开老奉天饭馆需要钱,我没钱就把咱家的房契抵押了。后来饭馆赚了些钱,我把房契赎回来。咱家的房契在我手里,您手里的房契是我托人做的假的。爹,您跟我说过,人这辈子哪有总是顺风顺水的,摔倒了再爬起来还是英雄好汉。我……爹!”
贺小辫病了,他躺在炕上看着两岁的孙子。孙子朝贺小辫笑,伸手揪贺小辫的胡子。贺小辫说:“揪吧,再不揪就揪不着了。孩儿啊,这一晃你在我贺家长这么大了,孩儿啊,我要走了,临走前我得嘱咐你几句,你那倒霉的爹不成气候,你将来要是有出息了,千万别听他的话,听了就是败家败国……”
贺小辫死了,贺义堂身穿孝服,泪流满面。祸不单行,他发现美沙纪和儿子不见了,赶紧跑到码头,看见美沙纪抱着孩子站在客船甲板上,就挥手高喊:“美沙纪!美沙纪!儿子!儿子!”儿子稚气地喊:“撒由那拉!撒由那拉!”
客船开走了,贺义堂的热泪流淌出来。
贺义堂提着行李箱从老奉天饭馆里走出来,他回头望向饭馆,把行李箱放在马车上。陈怀海走了过来说:“贺掌柜,您这是要回乡下吗?”贺义堂翻白眼:“是看我笑话来了吗?”
陈怀海说:“您要是不嫌弃,我那里有空地方,没人住,您可以住过来。”
贺义堂说:“陈掌柜,我贺义堂就是再破落,也不至于没地儿住吧?凭我这一身本事,在哪儿混不到一口好饭吃啊?我那瓶酒给我留好了,早晚我得回来喝个痛快!”说着上了马车。
————————
老二两站在山东老酒馆内窗前喝酒。拔树酒客走来望了老二两一眼,然后坐下高叫:“半斤烧刀子,一盘酱牛肉,再来一杯白开水!”拔树客看老二两把酒壶放在窗台上走了,就往老二两的酒壶里倒白开水。
过了一会儿,老二两回来,拿起酒壶倒了一盅酒慢慢喝,细细品,神态自若,嘴里叨叨咕咕。拔树酒客偷笑。
三爷对陈怀海说:“兑了水的酒老二两没品出来,看他整天喝得劲劲儿的,还以为他的酒道多深呢,原来就这两下子。”
陈怀海摇头:“绸缎眼皮儿看人,轻薄了不是。他品出来了。”
又一天,老二两站在窗前喝酒。拔树酒客坐在一旁瞄着老二两,看老二两走了,他又往老二两的酒壶里倒水。
雷子发现了,走过来说:“你干啥呢!欺负人,我揍你!”陈怀海过来拍了拍雷子的肩膀,摇摇头。老二两走回来,到窗前倒酒喝酒,依旧神态自若。
拔树酒客说:“和尚不急太监急,笑死人了。”陈怀海把手搭在拔树酒客肩上:“走,去那边说几句话。”拔树酒客甩开陈怀海的手:“有话就说呗,怕什么。”
陈怀海说:“今儿个你的酒我请了,往后请你不要再来。老酒馆不欢迎你。”
拔树酒客说:“陈掌柜,我逗那个穷光蛋玩儿呢,你有必要这么认真吗?不是吹牛,我一个礼拜的酒钱都顶那个叫花子喝一年的了,你不护我还护着他吗?”
陈怀海说:“进了老酒馆的门,来了都是客,一钱酒是情谊,一斤酒也是情谊,不分薄厚。老酒馆不撵客,可绝不留无酒德之客!”拔树酒客低头走了。
老二两站在窗前喝着酒,嘴里依旧叨叨咕咕……
————————
老酒馆里挺热闹。那正红和三个朋友围坐在桌前,喝酒聊天。几个朋友都夸那爷,给那爷戴高帽子,给他敬酒。那正红满面红光:“兄弟不分彼此,今天这酒我请了,谁争我跟谁急!”
杜先生走过来说:“那爷,您面泛红光,有喜事?”那正红说:“朋友在一块儿喝酒,不就是喜事吗?”杜先生笑着:“那我得离您近点坐,沾点您的喜气儿。”
那正红一脸醉意:“这嘴巧的,听着就是舒坦,杜先生,你的酒我请了!”
又有两个酒客过来打招呼:“哟,那爷,您在这儿呢!”那正红醉眼蒙眬:“您吉祥,这一晃眼儿,全是熟人啊,三爷,今天这酒我全请了!”那正红那桌的人越来越多,围成了一个大圈。
昏黄的灯光中,雪花飘飘……
那正红一个人坐在桌前,靠在椅子上闭着眼睛。雷子过来:“那爷!我们要关门了。”那正红缓缓站起,戴上皮帽子,穿上皮大褂。雷子搀着那正红走到柜台旁。那正红摸了摸兜:“先赊着吧。”
三爷说:“那爷,您都赊小半年的账了。”那正红皮帽子摘了下来,放在柜台上,又脱皮大褂:“酒菜钱。那爷我是欠账不还的人吗?要是传出去,让我这张老脸往哪儿搁啊?收着!”
三爷说:“那爷,您这可就为难我了,赶紧穿上吧。”“一码归一码,老酒馆还是老酒馆,三爷还是好三爷,咱们还是好交情,我还得来!”那正红穿着单褂子灯笼裤走出去。雪花飘飘中,那正红的笑声越来越远……
那正红回到家里,老婆埋怨:“这酒喝得把衣裳都喝没了,我看你早晚得把房子也喝进去。”那正红坐在桌前喝着茶:“你懂什么,钱是死的,人是活的,人家喝了你的酒,吃了你的饭,都会记得你的好。”
忽然有人敲门。老婆开了门。陈怀海提着一个包裹进来。那正红站起说:“是陈掌柜啊,您吉祥,请坐,看茶!”
陈怀海把包裹放在桌上:“那爷,您不要麻烦了,我说句话就走。昨晚我不在家,回来后得知您把衣裳落我那儿,我给您还回来了。”
那正红摆手:“还回来干啥,赶紧拿走!你把它还给我,就是再不让我去老酒馆了?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收回来里面也掺沙石了。要不你把它带回去,要不拿去烧了。”“那爷,您不要为难我好吗?”陈怀海放下包裹走了。
第二天一早,那正红就把皮帽子、皮大褂拿到当铺柜台上。
董掌柜说:“那爷,天还冷着呢,要不先留着穿吧。”那正红说:“家里满柜子都放不下,占地方不说,万一被虫子嗑了,倒是添了堵。这点事还磨叽啥,赶紧的,我还有要事办。”
董掌柜说:“那爷,您这皮褂子……”那正红话匣子打开了:“这皮褂子面儿上看,普普通通,跟平常之物没啥两样,可要细说起来,讲究多着呢,能冒您一脑门子汗!三十年前,我在宫里教小王爷们摔跤。那年冬天格外冷,呵口气舌头上站冰碴。旁人都是里三层外三层捂得严严实实,而我是短衣襟小打扮,身上还冒着热气。那时年轻,身上又有功夫,火力旺。我教小王爷们摔跤,一教就是一个时辰,从头练到尾,能不冒汗吗?可这汗不能总冒啊,一不冒我成了霜人了,浑身白花花一片。教完小王爷们,我正赶着热乎气儿往回走呢,只听一声断喝:‘站住!’我站住顺声望去,一看我这腿就软了,是皇上!皇上说我还纳闷呢,这雪人咋自己走了呢,成精了?原来是个人啊,吓我一跳。惊着皇上了,这可是死罪啊,我吓得大气都不敢出,等着发落。皇上问我怎么弄得跟雪人一样?我说是教小王爷们摔跤热的。没想到皇上乐了,说热成了雪人,这事不看见肯定不信,必有欺君之嫌,可到眼前了还确实为真,栽培皇子皇孙,尽心尽力,功劳不小,万不能受寒中病,赏皮马褂一件!皇上怕我冻着,赏我皮大褂,就从这件事上看,皇上宅心仁厚,让人感念啊。”那正红的眼睛湿润了。
董掌柜说:“那爷,您这大褂是宝贝,还是别当了。”
那正红火了:“住口,你怎敢用‘当’字!要是被皇上听见,就得砍了你的头!”董掌柜冷笑:“您把它拿我这来,不就是要当了吗?这都啥世道了,皇上在哪儿呢?他管得着我吗?砍得了我的头吗?算了,这宝贝您拿走,我不收了。”
那正红愣了一下:“掌柜的,您别火啊,咱有事好商量。都是老相识,至于说翻脸就翻脸吗?来来来,咱老哥儿俩好好唠唠。”(完)
内容由“作家出版社”提供<部分> (严禁转载)